|
|
 发表于 2021-2-22 18:48:08
|
|阅读模式
发表于 2021-2-22 18:48:08
|
|阅读模式
来自重庆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安陆网。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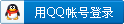
x
云雾像水打湿的棉被,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偌大的别墅里,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惟一的客人是李白。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
& Q1 z4 W5 V7 ?' a, ]+ Z/ k. g1 {5 s+ T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女冠,就是女道士。当然,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因为,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
! j, N: f* Y! p, h: {4 O5 U& N P, O' U! j
李唐重道教,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公主中间,就有不少人就痴迷于修道,甚至进而出家做道士。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乃同父同母所生,地位十分尊崇。年轻时,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唐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后来赐号持盈法师。终南山中的别墅,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 G1 i7 g# v c8 N1 r0 E! y% B R
( P# K- v6 r% u* X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拿着许氏的信,找到许家一位远亲。远亲官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给李白出主意说,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不妨找找他。张说身居高位,文章驰名天下,他受封为燕国公,与许国公苏颋——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已经六十四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海上钓鳌客。
$ Z7 u3 `+ D; T. I6 B X6 A8 }
, B" y5 O# W4 u5 n& X4 [ b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问他,你要钓鳌,请问用什么做线?用什么作钩?% F \9 i: \8 u% E( b
( y9 T( }6 n7 G! ?
李白长身玉立,侃侃而谈,回答说以虹霓为线,以明月为钩。* J7 d: R$ [- y4 ?
) D1 j& T5 p4 S# i7 e2 T: X8 k/ y张说又问,用什么为饵?4 ?! v- X6 X9 `1 w: z. m5 R, ~
- D! l: E" D. I( a
李白答,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c! a/ l2 b5 B) m2 H9 h
8 X) R& F5 T7 O
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虽然没有举荐他,但把儿子张垍介绍给了李白。张垍不仅是相门公子,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
3 l H) z9 V0 f& K1 W) ]0 \7 y9 Y# y6 D% S6 u, ^
张垍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那个热心修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她十分喜欢王维的诗,王维借助她的力荐,一举中了状元。对这些京城往事,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 m# _ i4 X0 m. N
! ^4 C7 B3 a: F" l! e$ ^
所以,当张垍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墅时,李白充满期待,他甚至能感觉得到,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他即将跨上彩虹,一步登天——从年轻时起,他就不屑于像普通官员那样一步一迁的按部就班,而是立志要像管仲、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立抵卿相。
7 B L2 ~' X& s! ~6 C" e$ ?! ]' ^" i; U/ G7 P( y' `* J8 a+ h
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李白为尚未蒙面的公主写诗,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想象她修仙习道,行踪无定,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神秘莫测。
& G* d1 ^% s0 s4 O
9 z) b. a6 j# V) s( I3 \ ]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然而,一等数十天,玉真仙人毫无踪影。后来,他从看守别墅的仆人那里得知,事实上,玉真公主已经一两年没来过了。失望之余,李白隐约感到被张垍骗了,可他只能给张垍寄两首诗,含蓄地发发牢骚。张垍没有回应他。李白只好离开。“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的终南山恍如梦魇。8 |! u! s/ \5 V
# P8 t- _9 E( r* w( y$ l. f' S. T e) d, i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与唐代其它诗人如杜甫、高适、李商隐、韩愈、等人相比,李白的确更热衷山水。他的热衷山水,既有因好道而“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成份,也有因发自内心地对或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6 Q5 a# Z+ Q' d# }4 @4 `2 n% p4 t
/ {9 `5 Z: L$ k; ?( K1 d6 m+ G l从终南山下来,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坊州等地,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心情稍稍平复后,他重返长安。意外的是,许氏远亲避而不见,张说去世了,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 }3 q) r/ ~& A! j, E
8 U! f$ `. l3 ]" l
幸亏在坊州时,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靠这笔钱,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大约干谒无门,这一时期,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为此,他遭遇了北门之厄。
1 H( `) `4 D4 G) e2 @8 r5 V/ e
9 U$ [" e [7 A5 G5 w: v- v6 G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李白虽会剑术,然寡不敌众。正在危急时,陆调纵马奔来,把李白救走;旋又报告官府,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9 \& J8 d' i" \6 h
: O2 s2 F4 H+ v1 Q* S经此一折,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不仅对长安失望,甚至,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他在《行路难》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方面,他既安慰自已:“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另一方面,他又仿佛看破红尘,心灰意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的一生,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R8 v2 l1 ^( v- g! b. T" ^$ i+ Z; c
" X( p3 i' R( q, v, z: g1 I731年暮春,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不过,他没回家——尽管在长安期间,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但是,他不想回家,也无颜回家。毕竟,在长安一无所获,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无论是真关心的惋惜,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
2 T9 S& z2 t% p$ x9 v( S6 @' s' E/ Z& E K* K( d: Z8 U. Q
李白向东而行,经东都洛阳,折向东南而至宋城(河南商丘)。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梁园。关于梁园,还有一段题外话。十多年前,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看到一座门坊,上书:梁园。开封不少地名,也冠以梁园,或梁苑,如梁园小区、梁苑小学。甚至,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也称梁园在开封,就在古吹台一带。
5 j7 T+ ~4 k( G8 P: _. \; v2 J& i+ `& }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园的始作俑者系西汉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甚受其母窦大后爱怜,地位尊崇。受封梁王后,建都雎阳,即商丘。梁王在世时,建设了一座方圆达三百里的园林,称为东苑、菟园,后人称为梁园,或梁苑。梁王雅好文学,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枚乘等网罗手下,出没于梁园。$ p8 @6 ^8 V2 P9 c+ _
# S. x2 Z; l" k" X
那么,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尽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开封,但更多迹象表明,梁园其实在商丘。因为,商丘才是梁国都城,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距王城却有一百多公里。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 F0 \/ ^+ R2 q; ]/ y5 P) ~! D
! y& [. N4 l; \: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然而到了故址一看,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吹一同消失。池水干涸,古木幽森,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的坟墓也被辟为耕地。既然人生如此,世事如此,他只好“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0 \6 {7 _ }. S
: w U* B! Z6 h其间的意绪,颇像汉代无名氏目睹了“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的无常后,发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感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不如即时行乐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因此在诗的结尾,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q4 Z/ }! s0 q9 b1 ?
' Z' ]( c6 H8 A6 K' c- ]& ]
颖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无名小镇,它虽无名,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颖阳到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颖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1 s8 m: n( z u- S$ Q
7 o5 \% [ `! r# n ?李白交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有一种说法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应约相见,要么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颖阳山居,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2 n7 J! \0 }* r2 V- }8 U( x. t' b7 u
/ Z, Q1 M- r u: I9 \( G2 F在颖阳山居小住后,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并结为知交。聚会结束后,李白不得不回安陆——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为期三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4 j4 S! O! F) f$ ?
[( V" r8 X# z2 O* }
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入赘女家的赘婿。一年多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4 C# Z( m- o: T
4 z- F/ k( ^" g I) x+ T8 w7 p, [
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汇合。按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C$ T+ C7 }; B, ~" B1 u
1 ^6 Y# `5 ?0 b9 s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这座如今的普通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不过,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很少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 U& E% I) z5 ]4 L6 \* O
3 \; U% z; a* V9 l# j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这个名字,来源于两千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由老城村向北,几公里外,黄河日夜东流,大桥西侧,耸立着一座高塔,塔身竖列红色大字: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
8 U2 X, X2 a3 n0 T& F# s G9 g' P' c( ^
由标志塔上溯二十公里,便是黄河的最后一道峡谷:小浪底峡谷。出了此峡,黄河从此进入一马平川的下游地区。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 W3 U3 H& b7 B2 y. y! Y/ c3 J2 Y% Q$ ]9 j
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口。汉语里,津就是渡口的意思。那么,孟津古渡在哪里呢?主流说法认为,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间的扣马村。 b" z; U6 M& f% C/ @
* Z0 O$ a" e L& P" g$ W u
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据说是武王付纣时,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村子里,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一方石头上刻着“商夷齐扣马地”。当地人说,老屋是明清时的夷齐祠旧址。
5 ]8 S; r: y1 a9 j' |7 a1 N" i+ l) E$ q- x9 z
作为洛阳周边最重要的渡口,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他只知道,要前往太原,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 ~ v# f: w. ?
9 [6 X# B, ^5 g0 n( Y( r9 [+ K. Y扣马村外的黄河,水流平缓,河面较宽,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唐朝时,供人们过河的,不是船只,而是浮桥。当时,利用水中沙洲,建成了两道浮桥,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维护浮桥的工作人员,计有水手二百五十人、木工十人。严耕望认为它是“中古时代南北交通第一要津”。
4 P- M% @9 e7 k* y7 E
: M/ |7 R8 y( z' Y+ D; ]; R' D8 Z% M李白和元结经过孟津浮桥,由南而北,大约只需步行两三天,他们便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7 X8 N' p6 \+ ^7 E9 F! \% w) O% g0 N4 n
8 O- C2 Q% \( o那便是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呈东北-西南走向,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有一年四月,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沁阳往北十多公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 ^ a v. _6 P) V3 t
, z! T% b2 s+ m- z I+ z; U7 G
当年,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公路斗折蛇行,时而爬上半山,时而跌进山谷。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年久风化后,坚硬的石头缝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 g9 f2 j' T1 J/ u( x( i2 ~
/ Z7 \, p7 g( t
与残留的古道相比,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羊肠坂的得名,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有如羊肠。
& {, N' o' L, n- n. ?3 m- d
/ }: |' C _$ v( t查史料可知,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却因扼京洛之咽喉,加之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曹操的《苦寒行》就写于此:“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很多年后,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 l, y6 s( e: a" c5 Z' B' |! ^; E/ q
, H1 Y9 y. V3 m" `8 v北游太原时的李白,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诗名却已遍及海内。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李白诗作表明,他在太原呆了一年左右。其间,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更多时候,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太原南边的晋祠,曾经多次前往。
5 C3 y5 m! I: Z5 F; y& i: f* ?$ [$ u5 y
晋祠极为悠久,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晋祠里,一株斜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自周朝时被栽种于这里,它已经在几十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两千六百年以上——即便李白时代,它也有一千四百岁了。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只是,有可能,那时,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1 f9 W4 ?3 d4 K* i
4 ?/ @+ Q+ \* W
在太原,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李白一直对自已的剑术颇为自负。他认为,如果从军,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甚至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 l+ y7 k. v1 A; ~+ l. p
' b% T0 u8 Q0 `& }元演制止了他。元演告诉他,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他的父亲守边多年,早该调回内地,可因朝中无人,很可能就终老太原。元演的父亲如此,他手下的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8 q6 V3 f" m/ y j
; Q- \' y: V8 n# }8 o* C9 P
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将军?白首没三边。”
2 y$ _- m/ p% o8 R* a
0 D: m. l( f6 }一年多后的初秋,李白辞别元府尹。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银两之外,还有一匹五花马,一件价值昂贵的千金裘。归往安陆途中,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并经元丹丘介绍,结识了新朋友岑勋。李白与元、岑二人痛饮之余,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将进酒》。诗里,他不无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7 Z4 n, V# m$ ~/ C% o% ~/ o$ {2 A0 a' K
5 h) A% v4 u: o! i6 E图片
1 _: Q( N$ |) p功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 R/ ]: F j8 O; R( V
图片
4 m, W- r* e# E* K4 p( o" q# x# J. s
: q, I! R4 _0 p0 G4 g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一入长安与二入长安之间,有十二年的间隔。李白从三十岁到了四十二岁。
( a- o ]1 a9 T/ }: Z3 _3 y2 i9 N# i+ N; {
四十岁前后两年,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人们常说哀乐中年,其实,以哀为主,以乐为辅。或者说,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从太原归安陆后,李白罕见地在家呆了一年。读书、写诗、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他很快就“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担心岁月流失,马齿徒长而功名未就。毕竟,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他年近不惑,实在是一个令人恐慌的年龄。/ D" ]( S4 v$ h+ M5 u
. G- T3 \! |) X: z" D8 F) Q
三十八岁那年,李白作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他先后在南阳、颖阳、宋城、下邳、扬州、杭州、温州、荆州、襄阳等地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陪他们喝酒,为他们吟诗、作文,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努力推销自已。
Z: {+ R3 ~; q5 a/ U
* ]2 C. B/ w' l/ T4 N* X4 \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为此,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空谒苍梧带,徒寻溟海仙;已闻海水浅,岂见三桃园”,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根本不准备落到实处。7 [! u" P% [( ~) V
& X, c' d! f! M* z2 Y- t# g/ c% Z( z三十九岁那年,李白作了父亲,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四十岁那年,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
# }8 ]7 o1 Y) ]. r, h
1 _/ n1 m4 V: t5 K- B8 w8 l; m# b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这年,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很可能要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
}/ m( b0 g% m! {$ G! v" l, i- E8 H* K
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此前,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痈疽的毒疮——现代医学认为,乃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曾就是得此病而死。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不料,王昌龄来了。诗友相聚,免不了觥筹交错,狂饮剧谈。要命的是,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鲜,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鳊。纵情之下,孟浩然忘了医嘱,大吃特吃。于是,悲剧了,“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而终”。2 i4 T' r7 e" g& i! J Y' c
& c s0 v' U0 `+ W
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那么,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李白结束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安陆岁月。这个人,就是许氏。许氏出身高门,自与李白婚后,聚少离多。当李白漫游天下时,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一个还不到一岁。# |6 D1 n7 q. R
1 f k! L! Z0 `3 b; M1 I* t* f. l
许氏既死,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对安陆这座小城,他大概也失去了再居住的兴趣。李白搬迁了。目的地是山东鲁郡,即山东兖州。选择鲁郡,很可能在于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
% a- Z* [$ b- ~6 Z% E: A. h, _, ~3 @4 A- A
到了鲁郡,在族人帮助下,他在瑕丘(今兖州市兖州区)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购了几亩地,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并且,最令李白愤怒的是,同居后,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竟然跟人私奔了。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 q( Q8 h# j. D6 c
3 x* m- o& l+ G1 A5 I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首先是反感他无度的饮酒。其次,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四十,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奴婢眼里无英雄,奴婢眼里也无诗仙。
* F) C& W6 b% E
0 L2 i0 s) y" d. j0 N. f5 Q郁郁寡欢中,李白去了一趟嵩山。那里,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今天,从兖州到嵩山,高速公路四百多公里,驾车约五个小时,但在李白的唐朝,至少要耗费十几天。餐风露宿半个月,李白赶到颖阳山居,不是为了聚会,而是为了告别——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
: g; D. f, e0 t/ g: X4 x5 ^4 y9 q2 l' h3 a$ R
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从兖州到嵩山,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李白如此不辞辛苦的送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
& K7 V: J' p! C% _& W/ L8 E0 v1 D( W; \
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向朝廷举荐他。 Y; K' L; s' B( j+ n3 [
' W, v6 \ S" G% O, z; N
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次年秋,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他一边杀鸡酌酒,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此时,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 Z; B0 R' X1 Z# U$ ~
; g+ W( u& G0 W; |, t4 x否则,李白出游时,谁来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而失态:# U. t2 k- r8 `5 w ^9 C2 N/ v
* q ]. E# C$ \2 _9 x. @5 P/ P: F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 F" ?, ?' T2 a) u* T$ X
- j: h' l. {5 Z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 ^6 c& _6 l ^. n- n" Z( I8 ~$ E( U- c/ F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 u! O) K" k! I1 c7 I
$ o' s5 l' b8 F"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 ^: Z/ d5 y' P2 i, s2 J$ ?7 ?
4 v3 W3 O& Z6 w! E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 Y! t3 b- F r( s0 N K9 \0 K
4 H0 O9 Q" a7 y2 g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8 P& |8 s$ u( H5 a6 B% s2 A
, d1 e8 c6 g0 p" g# ~/ S f5 z: n无论什么时代,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早春二月,燕子斜飞,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斜视的目光。
, \3 e, n. K9 n, U
) v( W2 ^6 t8 b- l1 y# M$ o1961年,经过四年多的发掘,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好多年的古城再一次浮现在二十世纪的阳光下。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极盛时,这里的居民至少在两百万以上。' F# N- J& y& {( g4 m# Z
% _) N, {4 o9 t$ Z, w
发掘证明: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七十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五倍。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4 t% w: L' I# i8 |7 c% s* ?% N: V8 ?
: t3 m( z4 R P! Z7 T1 R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朱雀大街的宽度,考古实测为一百五十五米,足以并行四十五辆马车。朱雀大街两侧各有五条平行大街,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每四条街道围合成一个个居民里坊,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用了这样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 X) g2 p0 _6 D# S
' r1 ^& p' X: P' H+ E顾炎武感叹:“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廓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廊舍之为唐旧制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3 C1 C& x6 o! E' j5 B/ G
! ~: L/ S9 Y! v, N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余下的城廓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周时奋先生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0 T0 E! }3 @; J* n- m, Z6 E9 h
3 N# Z# J1 {* Q: o& H+ a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出狠话,他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第一次,他失败了;第二次,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所以,他几乎算成功了。( Z# ?' t# a9 p* Z ^/ v
5 [" ~0 q* M$ D3 m1 g* j" q8 N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论才气或名气,贺知章都只能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若论爽快与真性情,贺知章却名列前茅。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结识了贺知章。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灵犀相通。+ V! o4 [, [5 U% Z b% C7 g
) W+ P/ z) Q) Z! z- Y* X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比李白大了四十一岁,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不仅年龄大,社会地位也高,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他在朝五十年,耳染目濡,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
- i0 I1 Y. a( L' m
( o' v6 h } i7 X2 Q,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却很深。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既得意又感动。后来,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李白为他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他不无动容地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2 v2 a7 n. s3 r. u9 A& }% v9 a# H+ I0 n6 @( }
纵情诗酒中,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从有关记载看,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李白进入大殿后,李隆基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 s. x F6 ~5 y# Y$ J1 ?$ [- U2 }& g* a3 b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有做到首相副首相一级的高级官员才有可能。然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院供奉。所谓翰林院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只要有一材一艺――斗鸡养狗、写诗作画都算――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严格地讲,它根本不算官,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
. n! D2 ?; x) ~- ?* e- w( {' ^6 Q! D, B3 h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其情其景,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而是她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
! U; A) v* ^+ n' s1 Q# D {
0 |5 {+ Z2 R4 K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
6 V. ?: Z6 i8 A* K5 v" Y
1 e' O" p7 L6 q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周敦颐说“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这年春天,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助兴的是宫庭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一时间丝竹如云,清歌如雨。唱得欢快时,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如此良辰美景,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 _: e' ]. \' e4 `, o- s3 A
0 l9 q8 s. R) E+ b5 f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地歌颂唐玄宗的盛世,他只赞美女人――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0 S9 ~5 c/ x) O
: s+ ]: ~! j( |$ U0 K. f: P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 m2 f5 S( `2 s; T+ S5 F) N+ d% F9 T& O5 ]! f# U t. l; d' t; L( F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 ]9 d1 Y% _4 x$ a$ |+ r, X* B q; d. R' a3 Y6 R) Q: a7 a1 t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8 N- \ p9 r9 T, C, Q
9 x6 p/ e- Q- x% v& L8 y) Z
坦率地说,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的光芒力透纸背,依然像李白的其它作品那样可圈可点。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文人要想安身立命,难免写点遵命文学,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李白的软肋,也是其它文人的软肋。惟因其普遍,才更觉辛酸。
: x0 g8 X$ u4 e0 C: ^# v2 m% w# y% I2 f8 p' J: l
二入长安,前后三年,近两千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
* U- |2 d- E& l4 j" R# C3 y
8 b& a/ D" Z" U$ s9 R翰林供奉位置尴尬,地位低下。这不是李白要的,更不是李白的理想。李白之前一千余年,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气话――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
1 K9 ]7 h1 O, A, C* e" h, l& q. U7 Q$ V0 q/ J
三年的张望与待诏,三年的酒局与饭局,三年的烟花与落拓,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公时,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对这位一生都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关节发出吱吱吱的生锈的声音。- w4 b* \7 t6 e; m/ Q
. ~7 L- i P0 U f) Y* b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这就是长安,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
7 w# b: S3 x, s
7 h( _: d, |6 E* h) b# Q/ n之前,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天宝三年(744),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以《送贺宾客归越》赠别――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者前往三千里外的故乡,既是生离,也是死别:4 s# t$ e) n. u* c) C: M0 G/ J
* Q$ }) {/ E$ o. F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Q) E6 `5 Q5 |# _; G/ }; ?1 {3 Q
5 g/ }" G+ X- P) ^- m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T9 x5 [; T$ f/ I/ h
8 o. |, {- ~! I% C# k7 ~0 Z; O8 F S4 W+ w3 s: _) U
图片* M% Z1 k, e& L1 c$ U
江湖: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 I& F+ @ H2 L! K0 l! v& I* D$ ]图片) [7 w6 g3 I6 P9 i e
A7 h, s# c7 Q# w" d% r% O& h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
2 j9 K! `6 ~; T' x# H在我看来,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三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 M3 K& o( a# U7 y( a' h" q
+ U( c1 q/ S2 h- u1 j1 A
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载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y7 R! ~% ?* ]4 M+ e0 k
! S5 f3 @: l8 V* J0 E4 e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将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
& g4 @' n) K5 q( b% e' N
8 m& T8 ?- Q2 M9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而变得格外昂扬外露。大师也不例外。7 R7 o9 a( ]2 ^/ \! s+ r; K5 @
. N! x6 w, R% n1 T: x {6 |; i% w+ J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 k- i' y& \) G, i6 S7 k N
4 y- e+ {1 W3 O A7 u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载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L/ Z/ g# \3 E. e8 y
* Q. |! _6 }3 S5 }: l( y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比如席勒与歌德,福楼拜与莫泊桑,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
^/ X9 U# n9 _ A8 o) d; `1 L2 a
* C+ O& _/ ^$ ~1 F8 s* x U3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十一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无端地,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那么李白长身玉立,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 `0 p! R, N! a' ]2 ~0 F) k" {4 {
6 ]( @8 n2 \: q' D7 z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两个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的人。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朗照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Q/ [4 D' q+ ?! T0 s' d
2 q6 I0 W0 e, H& I7 ^9 l有论者以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理由是杜甫写过十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长兄性格。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日后仍然会反刍似地在李白心里中游荡,如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 N# Y9 A+ P; _& l; i* a
. r Q/ Q3 A. o, _, n/ V% r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4 F$ {3 U; J8 T ~2 R2 d
" C! {" Q v0 S# R; L5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 ^! i a* J9 X, W' C& E9 ~
1 j% B$ m$ k+ }0 L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G, F/ M. l7 ]
1 I5 t0 P% M5 D& S+ Y8 y8 W u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 m/ c! {' ` }% t8 c4 P/ m0 F
6 n9 ~# w( n' \) Q2 G/ H+ g4 k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唐才子传》称他“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年轻时,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这么一干,名气却更大了。
) |' ]; X! d! h% V! Z' w7 N: X* H) M7 l% F! Y/ L) d- P, m. P
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因缘际会,出任蜀州、彭州等地刺史,官终部长级的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仕途甚为得意,以至《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8 q# `# w% p1 E% z7 {8 l, a* u9 s: u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那就是与杜甫相比,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友谊也有轻重。4 l! [& q2 r; E4 d$ K3 ^ M) `% M4 W
. q8 b6 m/ h6 A* C
粗略疏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
+ T: L$ n- T0 j4 f
3 O9 X% L6 I( p" v天宝三载初夏,李杜初逢于洛阳。几场剧饮后,二人分手。不久,两人再次相遇,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三人一起漫游梁宋。
4 O0 i0 W9 B8 z2 {0 n& o
$ ~1 ^, t* O& ^6 M2 H6 M) ~8 m4 e天宝四载春天,三人同游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说起往事,李邕一再致歉。5 e3 h, S- Q$ T" F3 o7 P0 o: r8 E: I
2 ^1 B) n' @+ r; e1 L% b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
) Z" [/ r7 x M# y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余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它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经“比你阔多了”。
- ^, g4 ~* K; g4 M2 q6 I" ?9 z' j6 `7 ~* v& y& }6 x) N q1 d
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有些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名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作吹台,一直沿用到今。2 C1 S9 x9 A5 n
# ]# o% F# @( Z' X- Q) x* M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 W: p- @7 {2 W, m; w0 i8 b* t! g
: e6 ~" `. f% I1 t( m) @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看来,当时世人眼里,李、杜、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 f, x% |5 E' m
2 y8 M2 N$ c# |2 f" V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庭。
) [: P, `/ N0 w6 z8 j2 l/ ?" ^5 j V9 [
李白、杜甫,还要加上一个高适,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 ~* m: K' T7 z9 F- _& [: Z+ _" Z8 I7 t$ c' Y% K
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明朝开封巡抚毛伯温有感于李、杜、高同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诗人们也蠃得了一席之地。5 L$ x+ R3 E: H# }) S
. c6 @0 V& a* U' ]
高适告辞后,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此后,两人分手。过了不久,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为此李白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亦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8 C, o- o) }! V1 O+ c& O1 V; x; b
8 N, E' y. [2 u: X; A# C" u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公路延伸到山麓时,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石门山。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石门山并不算知名——当然,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这里撰写《易经·系辞》的话,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四百米的小山肃然起敬。
) r( I5 `1 k, R/ j; n7 F5 c- e u, ~: o8 w3 H9 p
那一年,漫游、剧谈和狂饮是李、杜的常态,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划上句号:天宝四载深秋,分手的时候到了。――此前一年多,他们也经常分别,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嘎然而止了。
; J# H* [4 x6 X5 `) p' e; d
; b7 E; O4 @+ @$ `- v在石门,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离,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如同春天的古树;李白将漫游东南,好似日暮的浮云。4 d' s8 e+ w' M q( W3 p
( a" n( I' c4 E4 ^' N/ W S2 G4 I欧文·斯通说,“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诚哉斯言。对于告别的悲怆与隐痛,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石门一别,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7 e) h* w! K: j& s) L9 X$ I$ k* t' l' ^6 b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8 T N' M) s9 b/ {7 ?4 J% B, p* i( v( L/ d0 }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Q. r8 s! E5 r9 O2 s5 a
2 D4 v J3 o6 m% U' e: J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7 [- f4 n( R$ L" s( @% _
3 Z4 I5 S; v* `% z5 P; R/ q2 H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 z+ b& \# Q9 x6 P, A( d
; r8 p% N& D/ J0 t$ k q在石门山,李、杜以一场酒告别——尽管他们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但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2 b8 B' Q V, c: y- `$ o
" L4 O5 b* ^! B8 h' E8 {" L4 r ~ u3 y; ~石门一别,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交通极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武器。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岁月里,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漂零的流金岁月。
" ?+ ?# V/ }4 k D+ n
) O, K' \( A0 r7 u9 [6 P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首推写李白者。多年以后,杜甫在历经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世辛酸后,头发花白了,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这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诗题直抵花心式地就叫《不见》,题下则注“近无李白消息”:
, Q6 Y+ R7 G8 v# H. x/ e9 u3 S1 U& H% N# }, q% U
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2 @3 w" u: _. s7 m: G# F0 ^
- h6 S8 W" a( I2 M& @& X; O7 ?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 i, X, z' k+ w- U
$ e+ J3 O* ^/ h' t. a; {; r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M9 [! s9 m8 u- e
4 D8 j; ]: t3 a# |5 }- U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 J8 I: s2 ^6 y0 t! @* G* }4 z: [: ^( S# `8 s4 [2 {
【本文转自聂作平的黑纸白字,已刊于《新华每日电讯》】
4 [$ _! N8 L: n T, a! r: e% }6 ]3 S6 @( D9 { _7 g

$ L0 |% \4 |$ F& E
5 @1 H% e8 a/ Z2 R$ a |
|


![]()